《浪跡天地》:再思液態社會與流徙者

號角月報加拿大版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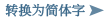
下筆這篇正值中秋節。我望月心忖:對很多人來說,「人月兩團圓」在今天複雜、動蕩的世界裡會否只是遙不可及的願望,甚至是令人傷感的嘲諷?戰爭、政治逼害、移民與難民問題、全球經濟變化,導致大量人口離鄉別井;⋯⋯這幾年充斥耳邊的是人們流徙、飄泊的新聞;這陣子浮現腦海的是獲2021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的《浪跡天地》(Nomadland)。
以四海為家展開游牧的人生
電影講述女主角Fern任職的美國石膏公司於內華達州帝國鎮的工廠關閉,而她的丈夫剛逝世。Fern變賣家產,買了一輛廂型車並展開游牧人生;她經歷打「散工」的生活,在亞馬遜公司工作,亦當過營地管理員和餐廳侍應。四海為家的她,有更多機會欣賞大自然,並結識了一班同樣過游牧生活的朋友,從他們那裡Fern聽到很多生命故事和掙扎,令她更深刻反省自己。但流徙的人生不是只有浪漫:Fern曾被嫌棄年紀大不獲臨時工、在沒暖氣下艱苦度過嚴寒、車輛壞了得向妹妹Dolly借錢維修。在與Dolly傾談時,Fern得悉妹妹渴望她留在身邊;同樣希望Fern留下的是曾浪跡天地,但後來與家人共住,並向Fern表白喜歡她的Dave。Fern在眾多流徙困難與安頓勸誘下,選擇重返亞馬遜公司工作、回內華達州清理家當,然後,駕車繼續她的游牧人生。液態生命及液態社會的流動
人曾對現代社會充滿憧憬:一切會是進步、穩定、正面的;但隨著工業革命、兩次世界大戰、近半個世紀前出現的新自由主義、「911事件」、難民問題,都令我們反思是否對現代社會有過分遐想。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以「液態社會」(liquid society)形容現代世界:傳統社會的結構和關係瓦解,變成流動、不固定的狀態。Fern的故事正描繪出液態社會及其中的液態生命:再沒「鐵飯碗」,事實上企業亦自身難保;當連租金也付不起,行駛的車輛就成了人有瓦遮頭的空間;人與人的相處和關係變得流動,呼應電影裡Bob的一句對白:「我在這裡遇過上百人,但我從不說真正的告別。我總是說:『路上見。』而我真的會再見到他們。無論是一個月後、一年後,還是好幾年後,我都會再見到他們。」導演趙婷多次用上遠景鏡頭,呈現Fern身處的不同環境;當中經常出現一幕,正是她那輛車在蜿蜒、仿似無盡頭的公路上行駛、流動。整本《聖經》充滿流徙的故事
趙婷對游牧人予以同情和肯定。電影片尾出現「獻給那些不得不離開的人。路上見」的字幕。她也似以角色的對白表達她對游牧人的欣賞:Fern到Dolly家與朋友燒烤,Dolly向朋友表示覺得姊姊像從前的拓荒者,繼承了美國傳統過著偉大人生;當Fern在商舖遇見朋友,朋友的女兒問Fern是否無家(homeless),Fern回答她非無家,只是無房(houseless)。事實上,Fern在旅程中認識不少如同她家人、互相幫助和傾訴的同路人,並不缺乏家的感覺。信徒確實要重新思考流徙者的生命。整本《聖經》充滿流徙的故事:亞伯拉罕的游牧人生、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們及後被擄的歷史,以至新約時約瑟和馬利亞帶嬰孩耶穌逃往埃及、耶穌在傳道時向門徒說「人子沒枕頭的地方」、《聖經•希伯來書》的作者指先賢「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流徙者的生命力與上主形象
《聖經》似乎向我們展示信仰的生命力,往往是在人認為不濟的流徙生活出現:流徙者也許更體會人的渺小,更懂倚靠上主,更知道信心和恩典是甚麼,更會憐憫他人並明白福音的必要和逼切。學者Peter Phan甚至認為,三一上主本身就是遷徙者(Deus Migrator):聖子「道成肉身」到世間體驗人間痛苦;作為生命賦予者並使歷史走向圓滿的聖靈是遷徙的力量;而聖父造物,本是把自己遷至危險境地,因祂要承受受造物對其叛逆與嫌棄。Peter Phan因此認為從流徙者那裡,我們更能找到上主之形象(imago Dei);而呼應做在弟兄中最小一個,就是做在耶穌身上的說法(馬太福音25章40節),他指擁抱、保護並去愛流徙者,就是擁抱、保護和愛三一的上主。液態恐懼與強人帶領的渴慕
不過,我們也需留意一些現實狀況。現實是今天大量流徙者攪動我們每一個的生活,這樣說不是怪罪、歸咎流徙者。鮑曼寫了一本書叫《液態恐懼》(Liquid Fear),指人在液態社會會自然地產生因面對不確定而來的焦慮;而流徙者的到來,也令本已擔心朝不保夕的「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at)感到威脅。在這情況下不少人會寄望一位強人帶領他們走出困局。鮑曼在一個訪問中表示,這就是美國特朗普上台其中一個原因,任何人的自由和保障應受重視,但這兩者往往存在張力。鮑曼說過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沒自由的安全是奴役,沒安全的自由就是徹底的混亂。」(Security without freedom is slavery. Freedom without security is complete chaos.)我們要嘗試拿捏當中的平衡,但這過程需時;我們今天需要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衝動的解決方案,而是願與他人對話的耐性,以及望見整體福祉的長遠目光。
 何兆斌博士
何兆斌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