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2》的多樣解讀、開放的《聖經》文本與懷疑的詮釋

號角月報加拿大版 二零二五年四月
逾越現實界線的滿足滋味
〈哪吒貳之魔童鬧海〉(下稱〈哪吒2〉)在今年1月下旬上映後不足一個月,已打破多項票房紀錄。很多影評嘗試探討它受歡迎的原因:有說電影一些對白,如「若前方無路,我就踏出一條路;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轉乾坤!」「既然他們還要我們的命,那我們就用這條命跟他們拼了。」或多或少捕捉到今天生活在政治環境不開放、經濟狀況欠佳的中國社會裡人民的痛苦、對自主的渴求、反抗的慾望,大大引發他們的共鳴。兩個多小時置身光影世界,使觀眾可擺脫現實裡的規限、束縛、壓力,令他們稍微嚐到現實中無法獲得的滿足的滋味。循這方向思考,借用法國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說法,〈哪吒2〉似為觀眾帶來一種「逾越界線的快感」(法文:jouissance)。這或許是電影吸引中國觀眾的一個原因。肯定既有愛國主義的快感
另一方面,羅蘭.巴特指文本也會帶給人肯定既有方向和前設、達致特定目標的的快感(法文為plaisir;英文為pleasure)。在〈哪吒2〉的情況中,這也許是一直存在的國家自豪感。昔日賣座動畫電影多由美國電影公司,如彼思(Pixar)製作;〈哪吒2〉的製作班底來自中國,而故事題材源自中國神話,加上動畫乘近期電玩遊戲〈黑神話:悟空〉以及人工智能DeepSeek的熱潮,使不少中國人覺得,中國的電腦科技有力跟歐美國家競爭,繼而發展出一種排他的愛國情緒。〈哪吒2〉在中國大陸上映期間,電影〈美國隊長4〉也上映。社交媒體出現了「哪吒在海外活不活無所謂,美國隊長在中國必須死」的帖文;有網友說要力捧〈哪吒2〉,並表示不看〈美國隊長4〉。一篇名為〈不是「美國隊長」不行了,而是美國不行了〉的文章,更有趣地指「在美國霸權的重壓之下,中國人民沒有屈服。」作者認為中國人像哪咤那樣「選擇了扭轉乾坤,選了嘗試改變這不合理的世界。可以說,〈哪咤2〉踏準了時代的脈搏,反映了時代精神,滿足了當今社會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也用『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鼓舞著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這論調跟我在之前提及中國人民不滿政府和經濟狀況的說法南轅北轍:前一個希望擺脫現實,甚至有反抗慾望;後一個則試圖用電影團結國內人民以對抗別國「打壓」;貼近中國政府取態的,當然是後者。
懷疑的詮釋與聖靈的引導
從以上對〈哪吒2〉的討論可見,同一文本可以生出多元,甚至矛盾的解讀。我們不必完全認同羅蘭.巴特「作者已死」的觀點,但這看法無論如何點出了所有文本皆有開放性,而因此而來的不同解讀會豐富文本本身的生命。〈哪吒2〉固然不能跟《聖經》相比,但《聖經》既是文本,自然也有類似情況。新教信徒群體,特別是華人教會往往對此感覺不自在,因很多信徒認為,上主透過《聖經》啟示的真理只有一個、是單向地從上主而來,且是永恆不變的;他們覺得若非如此,就會跌進相對主義的陷阱、意味「甚麼都可以」、等於宣稱世上沒有真理。然而,甚麼是「『一個』『永恆不變』的『真理』」?假如太快、太廉價地對此下定論,那就容易抹煞真理的複雜、多樣、豐富,而如此簡單地可被我們「掌握」的「真理」,難道真的是真理?我們要明白《聖經》文本有其開放特性,而上主容許我們對文本作多樣的解讀,但這樣說不等於相對主義。我們要做的,是詮釋學家利科(Paul Ricoeur)強調的「懷疑的詮釋」(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正如我們要存懷疑態度思考就〈哪吒2〉引發的不同解讀背後,可能存在的社會現實與人民期望之間的落差、觀眾既有的意識形態、是否擁有以及怎樣的政治議程等;這同樣適用於對《聖經》文本的解讀。例如讀《聖經•羅馬書》13章1至7節有關順服掌權者的段落時,我們會參考不同解釋:有說信徒無論任何情況都不可反抗政府;有說必須看上文下理,並了解這裡「順服」的用法;有指要清楚保羅當時羅馬帝國的處境,才明白為何保羅如此寫道。在參考眾多說法時,我們必須採取「懷疑的詮釋」,檢視解釋者—包括自己的經驗、慾望、前設、限制,甚至潛意識等,如何影響對經文的理解。
當然,身為信徒相信在懷疑中以愛和公義作記號的聖靈,會在過程中幫助我們作判斷。說聖靈引導我們閱讀《聖經》,非指「靈意」解經(這個對早期教父釋經方式的形容,如今已被一些信徒濫用及誤解為天馬行空的「隨意」),而是強調聖靈能幫助我們作出對應處境、具說服力、洞察力和生命力的《聖經》詮釋。
 何兆斌博士
何兆斌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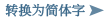
 何兆斌博士
何兆斌博士



